醫療信息化包含多個環節的信息化,如醫療服務的信息化、醫療支付的信息化、醫藥流通的信息化以及醫療器械器械信息化、醫療檢測機構信息化等。本文主要分析醫療信息化能夠從哪些方面助推未來十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重心從治病向防病的轉換及其背后的投資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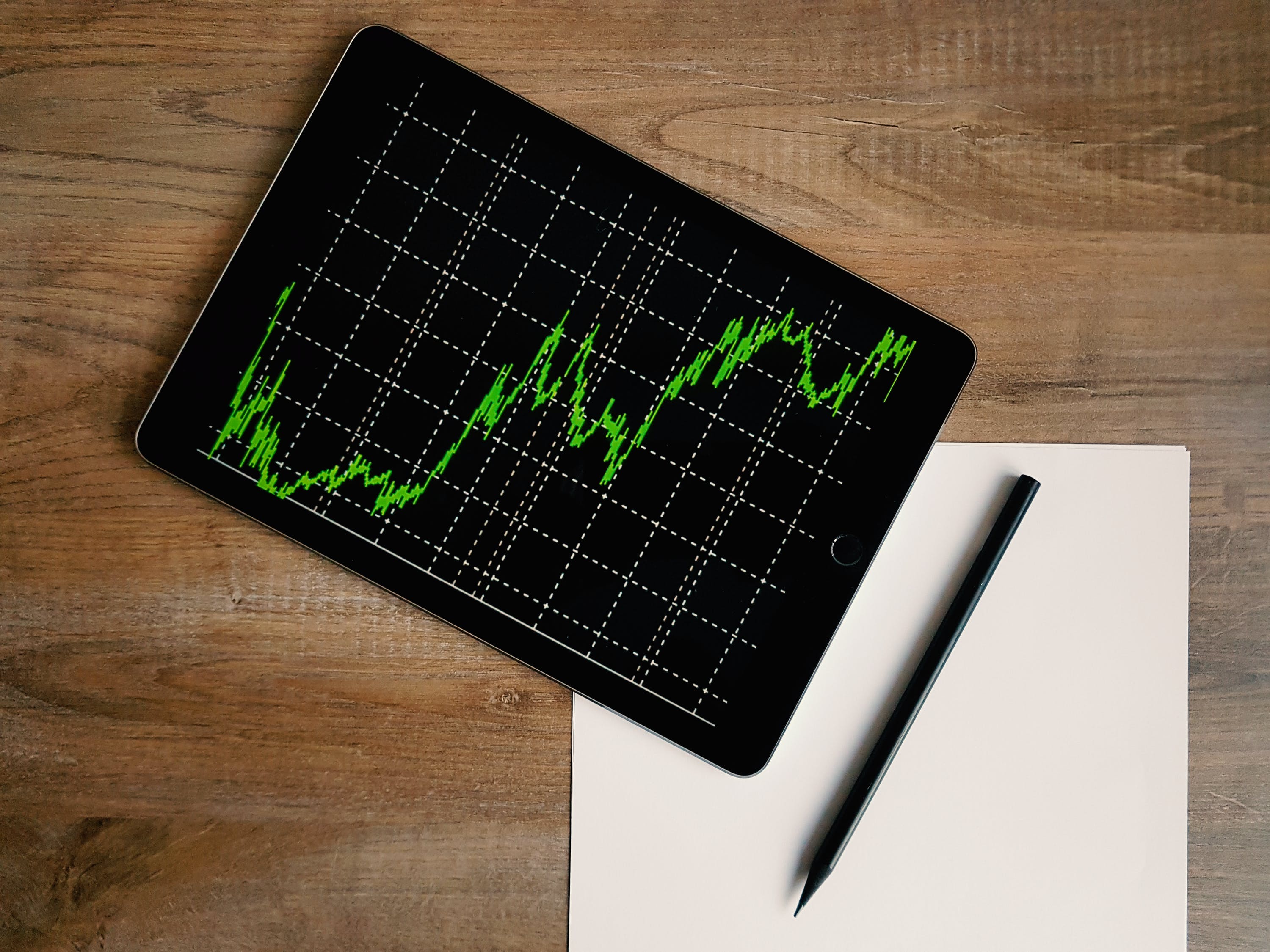
長期以來,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的重心在于治病。SARS之后,雖然在防病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從這次新冠疫情阻擊戰的情況看,我國“治病”為主的醫療體系建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導致“頭部”醫院負擔過重,普通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有效醫療服務供給能力不足。這導致后者難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應有的功能,影響區域醫療服務水平、醫療衛生體系運轉效率。

目前我國共有醫院33003所,其中三級醫院2548所,占比7.7%,三級甲等醫院1442所,占比僅為4.4%。但是三級醫院每年獲得的財政補助收入增速顯著快于二級和一級醫院。2010年,三級醫院財政補助收入為352.94億元,二級醫院為359.06億元,一級醫院為24.64億元。到2018年,三級醫院的財政補助收入為1532.79億元,二級醫院為1014.05億元,一級億元為61.36億元。2011年起,三級醫院的財政補助收入就已經超過一二級醫院財政補助收入之和。
從衛生人員數量看,三級醫院也遠多于一二級醫院。例如,2018年三級醫院的執業醫師數量為93.76萬人,一二級醫院執業醫師數量分別為13.12萬人和69.9萬人。床位數方面,三級醫院有236萬張,二級醫院有245萬張,一級醫院有58.5萬張。問題是,二級醫院衛生人員數量遠低于三級醫院 ,床位數更多并不意味著二級醫院有效醫療服務能力會好于三級醫院。產出依賴于投入水平,三級醫院獲得更多的投入,自然其醫療服務供給水平更高。這就造成患者集中于三級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就診。這導致頭部醫院不堪重負,而普通醫院的醫療資源不能等到有效使用。
2008-2014年三級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始終在100%以上,這意味著三級醫院長期在超負荷運行,同期二級醫院病床使用率不足90%,醫院病床使用率不到60%。2015年以來,三級醫院病床使用率有所回落,但仍在95%以上,一、二級醫院病床使用率仍維持在原有水平。三級醫院診療水平更高,群眾希望獲得更有效的醫療服務,這是人之常情。2016年三級醫院診療人次達到16.28億次,超過一、二級醫院診療人次之和。但是當發生突發高傳染性疫情時,醫院人滿為患,反而成為疫情可能的重要傳播場所。

其次,疫情的搜集、分析以及傳遞能力不足。事后看,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后,醫療系統對疫情的認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明顯滯后于疫情的傳播速度。這體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疫情初期曾經多日沒有通報疫情信息,確診病例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但是事后看,不少醫療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時間正式處于這一段時間。而醫療人員出現同樣癥狀的病情卻不能引起衛生管理機關和疾控系統進一步的重視,至少說明現階段醫療系統對疫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能有明顯的不足。
其二,由于疫情信息的掌握不夠全面,這導致初期對疫情的傳染性認識不夠,甚至還判斷未見明顯的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未能向社會預警,提升全社會防護意識。
其三,疫情上報后,衛生管理機關未能有效將疫情信息在醫院內通報并采取有效措施,導致初期疫情院內感染嚴重。本次疫情殉職的醫療人員來自于眼科、甲狀腺與乳腺科、消化內科,受感染的醫療人員也來自于不同科室。而最早上報疫情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由于防護措施得到,該科室無一例醫護人員感染,也沒有病人交叉感染。換句話說,當疫情已經被上報后,醫院之間對疫情信息的橫向溝通嚴重不足,導致其他醫院在疫情初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院感事件的發生。

總之,從新冠肺炎疫情來看,盡管武漢醫療資源豐富,但在重大傳染疫情之前,反而暴露出當地區域醫療資源的智能管理和信息共享的不足,雖然單個醫院醫療服務水平較高,但區域醫療服務水平、醫療衛生體系運轉效率還存在短板等問題。這些問題是與醫療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密切相關。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比較現實的解決方案是利用互聯網渠道,以醫療信息化的建設來有效分配醫療資源并加強疾控體系的建設。2018年4月國務院發文促進互聯網+醫療的發展。2018年9月國家衛健委發布多份文件,具體部署開展“互聯網+醫療”。新冠肺炎爆發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也要求利用“互聯網+醫療”來防控疫情,隨后國家衛健委連發三份文件以具體落實利用“互聯網+醫療”的措施。
醫療信息化或者“互聯網+醫療”之所以成為國家層面主推的解決現有醫療健康體系問題的應對措施,可能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醫療體系的投入不可謂不多,2018年衛生費用占GDP比重超過6%。醫療體系存在總量投入的問題,但資源配置效率矛盾現階段可能更為突出。第二,經驗對醫療服務供給水平有重要影響,再考慮到規模效應,全力支持“頭部”醫院建設有其必要性。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頭部”醫院的優質醫療服務更有效地分配到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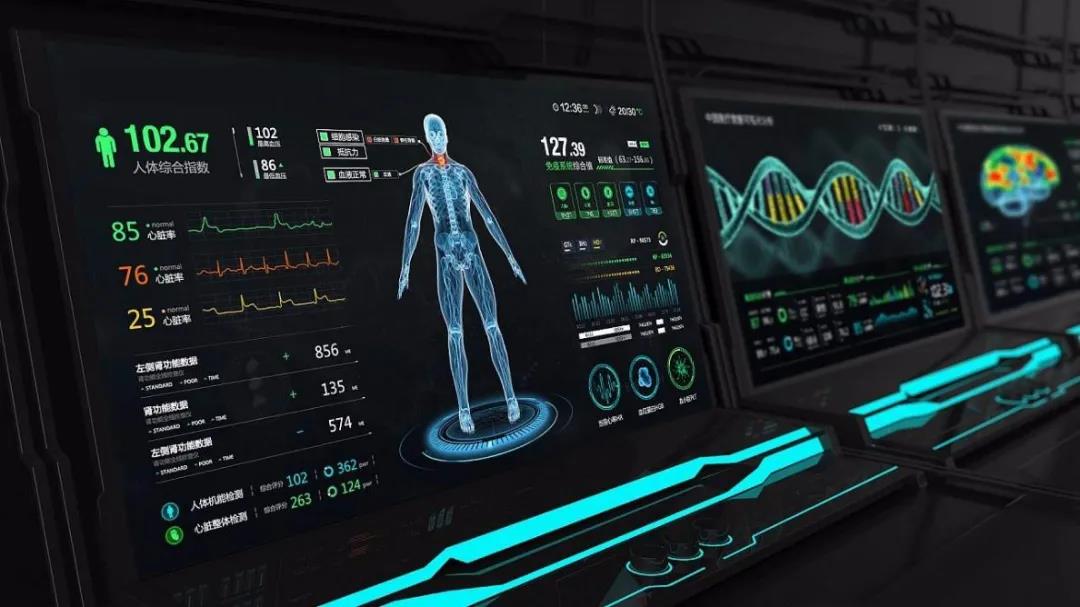
醫療信息化的基礎是醫院管理的信息化和臨床診斷的信息化,即HIS和CIS的建設。目前來看,公立醫院在HIS和CIS的建設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例如電子病例、電子醫囑已經較為普及。未來需要做的是,醫療信息的整合和大數據分析,打通院內、醫院間以及疾控系統的數據隔閡。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如果武漢各個醫院的臨床診斷信息能夠有效匯總,疾控系統可能會更早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從而為應對疫情贏得更多的時間,避免采取封城等極端嚴厲的措施來控制疫情。醫院內部各科室也會有意識地提高防護等級,合理分流病人。
醫療信息化將是衛生投入費用攻防轉換的重要推動手段。
首先,以在線問診、在線查房等“互聯網+醫院”模式避免患者集中于三甲醫院就診,提高基層衛生機構、一、二級醫院醫療資源使用效率。
其次,醫療信息化也有助于推動分級診療的發展。通過醫療信息化,實現患者就醫上下聯動,各級醫療機構分工明確,最終實現只有大病去醫院治療,小病和康復在社康中心的分級診療新格局,提高我國衛生健康系統的診療效率。

第三,醫療設備的信息化也是醫療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防控重要疫情發展,防治慢性病方面都能起到重要作用。還是以這次新冠肺炎為例,如果檢驗檢測設備能夠自動發送雙肺白化等新冠肺炎特征信息至疾控中心、醫院院感科,或許有助于相關部門更及時發現疫情的嚴重性,減少醫護人員感染。同時,醫療設備的信息化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醫院醫療設備的使用效益,降低醫療設備的維護費用和使用消耗,最大限度的保證醫療設備的充分使用和有效維護。
第四,醫療信息化也助于醫療用品生產廠商加快醫療用品研發、生產、推廣等。通過本次疫情的洗禮,一方面居民個人衛生意識有望顯著提高,對常見家用醫療器械的需求會相應上升;另一方面,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短板,不僅在于人員、經費,也在于醫療設備的配備方面。對于生產廠商而言,醫療信息化采集的大數據對于其精準開發市場需要的醫療設備是有幫助的。
第五,醫療信息化還能幫助醫保基金管理機構更有效控費。對于居民個人而言,治病或防病都離不開醫保基金在資金上的支持。然而人口老齡化下,醫保基金吃緊的現實意味著實現醫保基金收支平衡的緊迫性。今年我國已經在30個城市啟動DRG付費試點。所謂DRG,是指疾病診斷分組應用到醫保報銷管理中,是根據診斷病人性別年齡、疾病種類、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等不同因素進行分組,然后根據不同的組別進行付費。很明顯,合理的分組以及組別付費標準離不開醫療信息化的助力。

三 醫療信息化加速帶來的投資機會
醫療信息化在硬件投入方面的本質是衛生機構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遠程診療、醫療數據整合與分析等都離不開互聯網技術。因此,5G、服務器等領域均將受益于醫療信息化的建設。

從防控傳染病的角度看,智能醫療設備將可疑的傳染病跡象自動上報到疾控中心等公共衛生機構,有助于提早發現傳染病并及時防控。從治療慢性病的角度看,智能醫療設備實時采集的數據有助于醫療人員更準確判斷病情并對癥施藥。醫療設備制造業也將獲益于醫療信息化的加速建設。

中德澳智慧病房整體解決方案(從上至下:智慧護理交互系統、門旁系統、床旁智能交互系統)
03 設備維護服務
醫療信息化加速后,相關設備規模將大幅增長,設備維護的需求也會相應擴大。5G網絡、服務器需要定期維護,而醫療設備的維護也需要專業的維護服務。因此,醫療設備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會對相關維護服務需求有提振作用。
例如,公共衛生監測系統,醫療數據的整合、分析系統、互聯網醫療APP開發商等。針對衛生健康事業攻防轉換而言,軟件領域中,最核心的部分醫療大數據算法的開發。醫療大數據的利用水平是醫療信息化在防控疾病領域發揮作用的成敗關鍵。
總之,醫療信息化的受益行業橫跨制造業與服務業,至少包含醫療設備制造業、醫療服務業、信息產業。對應在市場的表現上,醫療服務業指數是過往10年醫藥行業中漲幅最大的行業。
作者:謝亞軒 張一平 原文標題:《衛生費用投入攻防轉換給醫療信息化帶來的機會》




